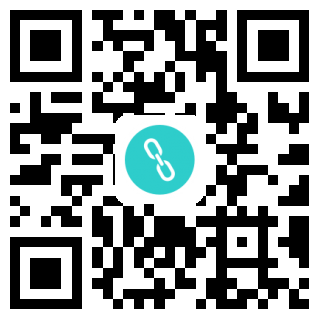吴方:宋文化的脱俗与从俗
剧场小世界,世界大剧场。从这个角度去看一个朝代的文化史,譬如宋代,不免会感到色彩光影纷披陆离,并且表现的方式、形态大不一样。各阶层的人们像是各不相同的文化角色,活动于不同的场合、“圈子”。不说理想、格调,风尚、趣味也是难以一概而言的。宋人生活的结构比较松散,比较不规范。譬如有人执于道德义理,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相标;有人忧国忧民,进退于廊庙天涯;同样是士大夫,有人则富贵乡里,脂粉队中,“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更不论大贾贵胄“买笑千金,呼卢百万”;皇帝不忘穷奢极侈,歌舞耽安;甚至在偏安一隅的南宋,也弥漫着追逐享乐的风气,士大夫不免一而悲歌慷慨,一而又以酒色声伎抑郁其无聊,或者隐逸于山水。种种或梦或醒,或悲或欢,或委曲或浅薄的文化体验、心理情绪在一个“大剧场”里生灭沉浮,他们“就像古希腊悲剧里的合唱队,尤其像那种参加动作的合唱队,随着搬演的情节的发展,歌唱他们的感想,直到那场戏剧惨痛的闭幕、南宋亡国,唱出他们最后的长歌当哭:‘世事庄周蝴蝶梦,春愁臣甫杜鹃诗!’”(钱锺书《宋诗选注•序》)
宋词在文学史上继唐诗之后成为一座艺术高峰,简单说,一是表现了用别的形式难以表现的审美感觉:准确、敏锐、深切、细腻;二是在具体而抑扬变化的长短句子组合中含蓄了普遍的人生感受和文化性格。前者,王国维的看法可作为说明:“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人间词话》)后者,如况周颐谈到的“词心”“词境”,实际也就是讲宋词风格与文化性格、时代情境的关系。他说:“吾听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已者在。此万不得已者,即词心也”;“人静帘垂,灯昏香直,窗外芙蓉残叶飒飒作秋声,与砌虫相和答……斯时若有无端哀怨枨触于万不得已;即而察之,一切境象全失,唯有小窗虚幌,笔床砚匣,一一在吾目前。此词境也”(《蕙风词话》)。
词之兴起,原因不一。譬如有韵文形式本身求变的契因,如说律诗绝句渐成习套潜力无多,故转而作他体,以求新意。或者因为词有“近俗”及“小技”的出身,可以比诗更为随意地聊以娱宾遣兴,长于表现男女艳情。又,因为词是按曲填词,富于音乐的韵律变化。另外也有人认为,由于宋诗“言理而不言情”,便把抒情的功能交付到填词上去了,等等。总的看,“词体之所以能发生,能成立,则因其恰能与自然之一种境界,人心之一种情感相应合而表达之。 ……以天象论,斜风细雨,淡月疏星,词境也;以地理论,幽壑清溪,平湖曲岸,词境也;以人心论,锐感灵思,深怀幽怨,词境也”(缪钺《诗词散论》)。进一步说,词境比之于诗境,虽然自有表现内容上的短处,却往往在意绪上平添了委婉、含蓄和吟咏不绝之味。试比较晏殊的《浣溪沙》与题旨相似的一首律诗,便见前者杰出,后者一般:
词之盛,在两宋。一是体裁格式趋于丰富,由小令到慢词长调,二是趣味风格的多样,三是词人佳作大量涌现,四是由绮丽怨悱中转出文雅蕴藉,由闺中儿女之言到感时伤事,时见高迈俊爽而终归于韶华深秀,主题出现了“爱情青春”“身世家国”“山林隐逸”“人生感悟”等几大类。词心词境亦随着时代生活和文人意绪的变化而多有变化。大略说,宋词流派,由晏殊、欧阳修、张先的清切雅丽开其端,又有柳永之含情幽艳靡曼近俗;继而有苏轼的雄绝一世雄词高唱,沿此路有黄庭坚、陈师道下启南宋的辛弃疾、刘克庄等人的豪放词风。另一个系列则是一些精于音律和人工之美,追求纤丽精致的“专家词人”,如周邦彦、贺铸、秦观、晏几道、李清照,以及南宋的姜夔、吴文英、史达祖、张炎等人。以前词论有一种“豪放”和“婉约”的分别,也有讲“正宗”和“变体”的,讲“南”和“北”的,讲“情胜”“气胜”“格胜”的。宋词世界,确乎消息幽深,难以尽道。如果从文化史的角度去看,宋词的主要色彩和风格趣味,大略不出宋代文化既走向成熟又趋于柔弱困顿的范围,体现着迟暮的美和感伤的情怀;绮中有怨,艳外有凄,壮而悲,愤而忧,以至于由“千古兴亡,百年悲笑”的感怆,落到了“哀以思”的冷寂:“……西窗又吹暗雨,为谁频断续,相和砧杵?候馆迎秋,离宫吊月,别有伤心无数。《豳》诗漫与。笑篱落呼灯,世间儿女。写入琴丝,一声声更苦。 ”姜白石这首咏蟋蟀的《齐天乐》,为宋词之旅的孤独心音续下尤为沉挚的余响。
上一则借词论宋,似乎事有未尽。什么事呢?且再说,一是宋词的进境反映出宋代文化艺术活动的“文人化”,越来越讲究文雅蕴藉,“意内言外”,也就是说“脱俗”。二是宋代城市经济生活的发达对文艺(包括诗词)的影响,不算小,词既与生活所要求的一定娱乐性、刺激性有关,便不能不有“从俗”“近俗”的特点,譬如“诗雅词俗”的说法。这两条看起来十分矛盾,实际上也未尝不可以并行:前面的“脱俗”是就文人化的格调境界而言的,后面的“从俗”则着重于题材和语言方面。雅与俗,既矛盾又可以协调,互为作用,这大概是传统文化在趣味上一张一弛而馥郁酝酿的一种特性。
在这里,包括讲史话本(它后来发展为具有广泛听众的历史演义体小说,以史实为经、虚构为纬),表达上由文言到语体白话,方法上由言志抒情到客观描述,显然为文学传统提供了一些新鲜的趣味和表现领域。但雅与俗、旧与新、变与不变的冲突,显然也并不严重,它们沿着各自的路向各奔前程,虽然相互有吸收、有影响,雅与俗仍大体保持各自的经验世界,并且在许多传统观念(历史观念、道德观念)上是共同的。也正因为如此,俗文艺(如小说、戏曲)尽管在宋元以后日渐发达,在观察和体验历史、人生上面仍然受到传统意识的限制。而普通老百姓的历史知识,关于善恶忠奸的概念,也主要是从说唱艺术以及戏曲表演中来的,虽然早期戏曲(宋杂剧)尚不脱歌舞、滑稽、杂技为主的娱乐性质。
由中晚唐到北宋,中国文化并未产生特别深刻的变化,但如果说不免物换星移,确也因为社会组织结构中平民阶级的兴起、社会生活中经贸活动因素的增加,逐渐形成不同的文化圈。其中主要的有两个,一个是士大夫文化圈,一个是平民文化圈。前者趋“雅”,后者趋“俗”,似乎是双轨的,这种情况延续于宋代以后。当然“阳春白雪”同“下里巴人”并非完全隔绝,有时,士大夫也受“俗”的影响,譬如理学家朱熹等人的文字加入了许多白话、俗语的成分;同时民间文化也受“雅”的影响,如工艺器物讲究精致和素雅的风格等。然而,两个圈子毕竟各有其不同的文化功能,而且士大夫文化自然占据着中心地位,并把传统文艺推向一个独具士大夫风神趣味的表现天地。譬如苏东坡的诗文书画所达到的成就,为后代文人所喜爱。表面看其笔墨钟灵源于才气性情,实际上正是出世的理想和既难以入世又难以出世的体验塑造了这种不俗的文人形象。在宋代文化艺术活动中,这种“文人化”性质具有相当普遍的意义,所谓“超然乎尘垢之外,一新天下耳目”。士大夫的生活因越来越“文人化”而带有优雅闲适风度,在宋以后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文化风尚,士大夫的使命似乎并不都在于“修齐治平”上,他们同时是一种文化角色,把他们的生活艺术和趣味,作为超越世事俗尘的途径,带进传统文化经验中去,似乎正是必要的补充。
比如苏轼所体认的理想境界:“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赤壁赋》)又如欧阳修晚年号“六一居士”,客有问曰:“六一何谓也?”居士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客曰:“是为五一尔,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吾之乐可胜道哉!方其得意于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见,疾雷破柱而不惊,虽响九奏于洞庭之野,阅大战于涿鹿之原,未足喻其乐且适也。’”(《六一居士传》)在这种洒脱悠然的文人天地里,传统文化中的许多“节目”,都可说在宋代趋向成熟。
四是绘画的神韵与文人画之发祥。宋代绘画承五代成就而又气象过迈,并转发出山水花鸟这一中国绘画的主流,成为绘画艺术的巅峰期。如初期荆浩、关仝、董源、范宽、李成的水墨山水画,将写实与写意、技法与观念相结合,于传统中另辟蹊径,至于笔简气壮、景简意长的幽远宁谧的境界,形成“尺幅千里”。进而,在北宋熙宁前后,绘画的方法、风格又进一步朝着士人情趣和神韵品位方向发展,如苏轼、李公麟、文同、米芾、米友仁等以“墨戏”表现其“襟韵洒落”。苏轼提出了“士人画”的命题:“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许便倦。”(《苏轼文集》)这自然是代表了新的标准。米芾的“米癫”画风很逸放,除率然表现其天真神采外,无所关心。在文人画的心理背景方面,郭熙讲得够清楚了:“……林泉之志,烟霞之侣,梦寐在焉,耳目断绝。今得妙手郁然出之,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猿声鸟啼,依约在耳,山光水色,滉漾夺目,此岂不快人意,实获我心哉?此世之所以贵夫画山水之本意也。”(《林泉高致》)眼前景,胸中山,在士大夫心性与自然的融合中,似乎可以超脱尘俗,“其神与万物交,其智与百工通。”到了南宋马远、夏珪的山水世界,则更是在无限的表现中企图超越有限,借点染自然而巧妙地表现感情的韵律。所谓“韵味清远,不为物态所拘”,也正表明士大夫文化在宋代确立了影响深远的“尚意”“重韵”的准则风范,并在其中塑造自足的文化性格。